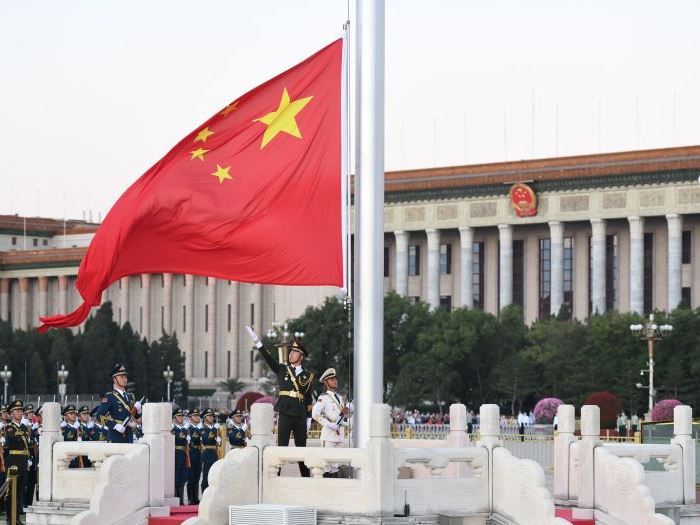
|
|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“穩定的善政治理” |
中評社╱題: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芻議(上) 作者:楊開煌(台灣),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、兼任教授
上世紀中國剛剛打開大門,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是第一次有機會,真正看到中國以外的世界領先中國幾代的西方國家,尤其是美國。當年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禁發出,中國面臨“開除球籍”的危機,從而強化了“改革”、“開放”的社會基礎,這使得全中國、全民族、全社會持續不懈地推動“改革開放”。從近代中國因應變局的歷史來看,“改革開放”是中國的“新自強運動”,加上“新五四運動”,在“改革開放”的大潮之中,中國不僅在硬實力方面逐步崛起,如今進入了軟實力的反思和崛起。然而反思比崛起容易,“反思”要的是反對,反得合理與否是次要的,“崛起”則需要創新式重建。從辯證法的“正、反、合”規律來比喻,“正”是原本的狀態,“反”是對立的階段,是必要的過程,但是“創新”才是“合”的階段,也是發展的真正的目的。
一、從“中體西用”到“後殖民”心態
晚清之際,中國連續迭遭西方國家的侵略,以致於清政府完全無法因應,名相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(1872年)提出“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的論斷,因而提出要“加強海防,以應對變局”。此時朝中大臣正在推動自強運動(洋務運動),這是當年的中國精英面對變局的方法,他們正在試圖學習西方的技術,即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(1842年,魏源編寫了著名的《海國圖志》提出的觀點),1861年(咸豐十一年),馮桂芬在《校邠廬抗議》中進一步提出“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,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”,1895年(光緒二十一年)4月,南溪贅叟在《萬國公報》上發表《救時策》一文,首次明確表述了“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”的概念。次年,禮部尚書孫家鼐《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》中再次提出,“自應以中學為主,西學為輔;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”。張之洞於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《勸學篇》,重申“舊學為體,新學為用”即“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”的方式以圖自強,對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。①
其後,他們主導的國家變革屢遭挫敗,從而“中體西用”變成後來中國知識分子嘲笑和諷刺晚清的“現代化”作為,中國人困惑了,迷失了,逐漸地洋務從“用”變成了我們想要的“體”,幫辦成為令人羨慕的工作,幫辦者也成為高級華人,以致“五四運動”之後“全盤西化”變成中國現代化唯一正確之道,而國、共兩黨學習、崇拜了不同的“西學”,而內鬥不已,然而在此氛圍下,“全盤西化”的選擇,成為中國人心目中唯一正確的道路之下,中國人開始全面否定晚清,進而全面否定中國文化、中國制度,甚至是自我否定,於是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所思所想就是“迎頭趕上”,這個“頭”是什麼,是“西方”,中國人把西方的今天視為我們的明天,中國人把學習溝通工具的“外語”,視為“知識”本身,中國全面地模仿、照搬西方一切,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教育、學術。為了中國的現代化,近代中國的“教育、學術”是西化最徹底也無爭議的領域,尤其是高等教育、研究機構,無不以西學為馬首是瞻,一切典章制度、人事規範、獎賞懲處,無不移植,無不照搬。其實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,在當前的西方主導的世界和世紀下,中華民族想要與西方並駕齊驅,既是迫不得已,也是不得不爾的辨法,關鍵是這些作為背後的主體性是什麼。此一主體性如果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我否定,盲目崇拜,那麼我們民族就永遠在迎“頭”,永遠在追趕;用現今的視角來看,“全盤西化”或多或少就帶有“自我否定”的情結,有了這種“情結”,就長期地、不斷地自我貶抑,自我渺小,失去對西方批判反省的能力,進入一種“後殖民狀態”,永遠地、絕對地肯定西方的一切,接受西方一切,甚至於肯定西方對中方所作的一切。“後殖民狀態”是指帝國主義對某個民族長期的殖民統治,造成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羨慕和崇拜,以致於一個民族雖已經掙脫了帝國主義者在政治、經濟和軍事上的殖民枷鎖,但是被殖民國家的社會和文化現象,依然餘留下前殖民國的影響,繼續統治著被殖民地區。“後殖民主義”就是針對後殖民國家的文化研究,以往的文化研究主要是為了理解被殖民者的內容,以便於殖民,然而,逐步透過文明/野蠻、開放/封閉、進步/落後、開發/未開發、現代/前現代等線型發展價值觀,使得後殖民的文化研究不自覺地證成了西方的“理性、先進、成熟”,而被殖民者祇是反例的對照物或參照物而已。而此一價值是同時注入和內化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內心,成為前者傲慢與後者自卑的根源。此一根源,尤其明確地表現在被殖民國家的學術領域,由於東西方在“現代知識”的創造過程中,並不是平等獨立的,西方學術界幾乎是全面掌握“現代學術”的典範,是以現代學術的問題意識、議程設定、學術話語、學術判準等方方面面,都沒有非西方的聲音,東方學術似乎是慣性地處於被動、追趕、邊緣與被檢證的處境,諾貝爾獎便是最佳的明證。
其實,從本質上說“中體西用”的應變思考,並沒有問題。首先,從哲學思考任何一個民族都必然也祇能從自己本體去認知外來文化,不以自己母文化為框架,根本無法也無從理解他者文化。其次,面對異文化的碰撞,我們是閉門抗拒,還是開放交流?如果是抗拒交流,故步自封,那就容易自大自滿終萎縮;開放交流才能截長補短、不斷成長。從此一角度來看,當年的西化派的精英們是正確的,我們不應該以今諷古,其實無人可以超越時代的局限,當今認為正確無比的抉擇,過些時日再評,答案也許不同。其三,真正的關鍵是如何實現“中體西用”之說,粗略地區分,可以有混合方式或是融合方式。
先說“混合方式”主要是指直接將西方的器物從購入、仿製以至於改進之後,由中國人使用:換言之,中國人用西方的器物、技術來促進國家的變化。擴而大之,進一步說照搬西方的制度、法規或教育等等套用在中國人的社會,也都是混合方式的“體用論”。這種方式本質上祇是追趕,而最大的成就也就祇能做到並駕齊驅。而且是長期受制於人。所以不論成功的程度如何,在西方來看,至多是從學生變成模範生;幾乎沒有機會從學生變成老師,而更加根本的問題還在於“混合方式”的一旦小有成功,(學得有點相似於西方)就會出現“被認可”的集體焦慮,即渴望得到西方的讚美、認同與肯定,從而每每以西方話語權來決定自己現代化的成敗。反之,一旦失敗,就很容易出現民族集體焦慮感,則令民族陷入迷失、虛無的自我否定,自我貶抑,把國家引向更亂、更痛苦、更分裂的深淵。從晚清到民初五四運動的中國,就是經歷這樣的歷程。總之,“混合方式”的方法,並無法使中國適妥地應變,之所以如此,主要的原因在於在晚清和民初當年中國處在隨時被瓜分、瓦解的危情下,中國精英並沒有足夠的時間真正理解西方的“現代化”,對如何把握中國的“體”的問題也沒法深思。客觀而言,在當時情境下“混合方式”的以變制變應該是最佳的策略, 然而歷經了“以俄為師”和“一面倒”的政策之後,實踐告訴了中國勢必另謀新策。
再說“融合方式”主要是指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性引進對方的文化,經過適當的改變,綜合和詮釋而發展出自己文化的新貌。此種創新必然也祇能在自己的主體意識下,對外來的西方文化進行選擇、吸收、理解、綜整、創新,簡言之,“融合”是一種創新的摸索過程,“融合”無法速成,“融合”需要時間;以中國近代的變遷來看,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從城市工人鬥爭到農民起義,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原本的無產階級革命,而毛澤東的工農革命理論的成功,是因為毛的革命符合了中國的國情。鄧小平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,如今才能有巨大的成就。所以改革有成,其實都是因為他所依據的理論不僅僅是“馬列主義”,還有中國特色。所謂中國特色就是從中國實情,從中國人民的需要出發去理解馬克思主義,所以早在八十年代初中共“十二大”時,中共就提出“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”的命題。鄧小平說:“我們的現代化建設,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,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,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。但是,照抄照搬別國經驗、別國模式,從來不能得到成功。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。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,走自己的道路,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,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。”②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重大議題上,把當代中國定位在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完全是依據中國自身的實際出發,再經過卅年探索,其間又加上了“三個代表”、“科學發展觀”等符合中國國情需要的理論修正,到了習近平提出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思想”的綜合性、整體性、系統性的融合式“中體西用”的新典範,從中國思考、把中國視為行動的主體,將馬列主義的理想和方法視為完成中國變遷的方法,而創新地提出“新思想”。此一“新思想”立基在鼓勵中華民族建立民族的“四個自信”(道路、理論、制度、文化)。
然而,在中國這個近百年遭受西方帝國主義欺凌到自信心盡失的民族,甚至可以說迄今依然深深受困於後殖民主義心態的民族,企圖重建“理性”的“民族自信”原本就是巨大的工程,必須滿足三個要件:其一是中國發展的實際成效;其二是中國政府的表現和倡議;其三是現實事態中,對比中西方的效果。在第一方面中國發展的實際成效,這一點已經無需太多描述,不論是以西方的指標,或是中國人民生活的事實感受,都證明了中國的快速崛起,而且在崛起之中,不斷面對問題,也不斷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。在第二方面中國政府的表現和倡議,在倡議部分,中國共產黨做了許多,“四個自信”自然是最直接、最簡潔的倡議。至於表現則是見仁見智的評價,不易有客觀的標準,但是從美國政府尤其是川普政權的反中作為,我們可以說,如果中國政府不能以“不卑不亢”的態度因應,美國的霸權主義在“反中”的作為上可能早就得逞,這一點大家應該都心裡有數的。至於第三方面,應該說對抗這場新冠疫情,為不同制度的國家面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治理表現,無疑是及時提供了明顯而清晰的佐證,尤其是中、美兩國的對比上。如果我們以國家必須提供給人民一個相對安心、安全的生活場所為標準,那麼中國的治理能力明顯地優於美國。這種優越性絕對不是簡單的領導人的作風、性格或能力的差異,最主要差異更表現在經由不同的政治文化,所形成的政治制度的不同。換言之,從“應急”的角度看,現行中國的制度是優於美國的制度。一旦中國人真正理解到中國自己的制度,在中國的發展和因應重大事故方面,確實是符合中國需要的制度,從而建立和提升中國人的“理性自信”,則其他方面的自信也自然容易建立。所謂“理性自信”是不盲目相信自己的標準是“普世”的,不會承認自己的標準是歷史的終結;相信自己的標準,必須與時俱進,必須因地制宜,必須因俗而易;所以自信而不是自傲,自信而不是自大,更不至於出現西方話語權所擔憂的狂熱的、擴張的民族主義。
當然在中國仍有若干執迷不悟者,如大陸的許多被稱為“帶路黨”型的所謂“公知”,更不說台灣當局到民間、絕大部分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的政客和“知識分子”,完全以“崇洋媚外”為唯一標準。所幸如今的中國上述三個要件齊備,從國家到社會,從精英到市民都具備民族反思的條件和氛圍,加上中國共產黨對此問題的重視,應該說有了較好的條件面對中華民族的後殖民心態。中國共產黨在2016年5月18日召開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”,總書記習近平提出:“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、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,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,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、精神品格、文明素質,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。…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,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、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。在這個過程中,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,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”③從學術中國化重建民族的自信心,應該是直指中華民族的後殖民心態病症中最為核心的問題。近現代幾乎全部學術學科的典範,都是西方學術界所建立的學術議程、學術分類、學術訓練、學術問題、學術方法、學術名詞、學術標準等,中國學界幾乎是全面移植,包括中國傳統的知識也必須按西方學術加以改造、包裝,學術的被殖民現象,已經“內化”為知識的“唯一”發源地,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從“學術層面”反省“後殖民”現象,是反省全民族的“後殖民”心態的預先性、基礎性工作。如果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不能重建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典範,則談不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,當然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。
|